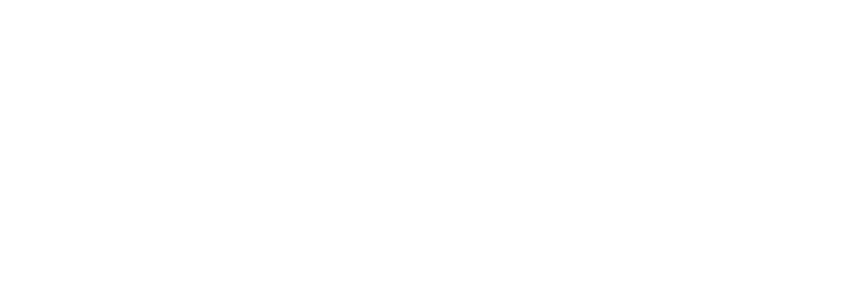导语|为何一次本应可控的集会,会在8月28日傍晚失控?
8月28日,雅加达国会门前的一场原定例行集会,最终演变为一次引发全国关注并波及多城的激烈冲突事件。当日午后,学生与网约摩的司机(ojol)在国会周边重新集结,夜晚时分,21岁的骑手Affan Kurniawan被防暴装甲车碾压不幸身亡。这一事件迅速点燃公众情绪,成为舆情“破圈”的导火索。
总统普拉博沃紧急召集高层会议,要求展开透明调查;警察总长Listyo Sigit Prabowo亲赴医院向家属致歉,并下令对涉事人员展开调查;与此同时,全国多座城市出现声援或进一步抗议的行动。这场事件不仅暴露了执法行为的边界问题,更折射出公众长期以来对“官民收入差距”“特权阶层特权化”与“制度性不公”的深层不满。
一、从“午前撤场”到“夜间引爆”:事件发展三阶段
白天:工会按计划撤场,劳工诉求平稳进行
当日中午以前,工会组织围绕最低工资、反对外包、税费负担等议题,按照原定安排完成了集会并有序解散,局势平稳可控。
下午:学生与骑手重新聚集,紧张局势开始升级
约下午2点后,学生与网约摩的司机开始在国会大楼及周边高架桥匝道集结,现场气氛逐步紧张。相较于工会组织明确的撤场时间表,后续聚集人群多通过社交媒体动员,缺乏统一组织。
夜晚:Affan死亡引爆舆情,情绪急剧升级
晚间,Affan Kurniawan在警方驱散过程中被机动旅(Brimob)装甲车碾压致死。其死亡视频通过社交媒体迅速扩散,引发全国震惊和舆论反弹。总统与高层迅速表态,要求透明调查并安抚情绪。
二、“特权政治”情绪如何发酵?——从议员住房津贴说起
此次事件所引发的民意反弹,远非一次执法事故所能解释。舆论焦点迅速从Affan之死扩散至更广泛的社会议题,尤其是“官员特权”问题。
议会为国会议员每月发放5,000万盾(约合3万美金)住房津贴,用于签五年租约、分12期发放。尽管副议长Sufmi Dasco Ahmad公开解释为“一次性分期安排,非长期固定”,但在公众看来,这一安排与最低工资之间差距达数十倍,引发强烈“体感不公平”。
更糟的是,财政部门与议会之间的“甩锅”姿态加剧了公众不满。财政部保持沉默,而政府官员对这一安排的解释前后不一,导致民众普遍质疑:特权的优先级究竟在哪里?是谁定的?钱从哪来?
三、火上浇油的几位“争议人物”与地方事件
1)总统府沟通主管Hasan Nasbi:失当回应加剧不信任感
自总统普拉博沃执政以来,总统沟通办公室负责人Hasan Nasbi多次因不当发言和回应媒体争议事件而招致批评。包括对《Tempo》杂志寄送“猪头”恐吓信事件的淡化处理,以及在国外媒体采访中对军队“涉民政”问题的强硬否认,均被批“缺乏同理心”。
他在4月提出辞职,但随后又考虑撤回,这种“进退反复”的行为进一步削弱公众对政府沟通能力的信任基础。
2)时任国会三委副主Ahmad Sahroni:“最蠢全世界”言论引爆舆论
在住房津贴争议高潮期,NasDem党籍议员Ahmad Sahroni将批评国会的网民称为“全世界最蠢(orang tolol sedunia)”,相关言论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刷屏,被视为“特权精英傲慢”的代表。尽管事后他发表澄清,仍难掩民众愤怒。
尽管该党随后将他调离原职位,但公众对国会整体“傲慢、疏离”的印象已然形成。
3)中爪哇Pati县长Sudewo:税费猛涨引抗议,点燃底层情绪
2025年,Pati县宣布土地税(PBB)与土地基准价格(NJOP)大幅上调,部分区域税负增长高达250%。当地研究机构指出,这一调整违反“最多3年一评”的法定原则,且在多年未调后突然一次性补齐,造成严重冲击。
此举在全国抗议声浪中,成为“基层税负过重、官民脱节”的典型例证。
4)“执政百日”争议人物回顾:多个高官言论与行为“踩雷”
多家媒体回顾总统执政“百日与半年”期间,列举了数名高官的不当言论与程序问题,包括:
- 对1998年历史的敏感性表述;
- 部门公文用于私人利益;
- 对环境问题的“非科学化”解释;
- 超常规预算申请。
在经济承压的大背景下,这些事件都被视为“政治精英与民众脱节”的缩影。
四、反腐观感遇挫?——特赦与免诉争议事件回顾
2024年7月底,国家通过大赦(amnesti)与免诉(abolisi)程序,给予PDI-P秘书长Hasto Kristiyanto与前贸工部长Tom Lembong特殊处理,引发法律界质疑。
尽管法理上,此类制度安排存在依据,但将其用于涉嫌腐败案件的行为,被舆论视为“政治调和”,甚至“反腐信号转软”的转折点。
多家研究机构与国际媒体指出,这种做法恐削弱反腐败机制的公信力,也进一步加剧公众对“权贵有特赦、小民不饶恕”的不满情绪。
五、为何8·28会“午后失控、夜里破圈”?——五个关键变量解析
- 视觉冲击强烈:Affan死亡视频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,成为道德与情感层面的“强触发”。
- 组织节奏脱节:工会按计划疏散,但学生与骑手多依赖社交媒体动员,缺乏风险评估与应对机制,导致警方反应滞后。
- “倍数政治”效应明显:议员住房津贴与最低工资的巨大差距,使“体感不公平”迅速上升为制度批评。
- 地方事件推波助澜:如Pati县税费激增等,使抗议情绪从首都扩散至全国城乡,并形成“生活现实与制度脱节”的共情基础。
- 资本市场反馈放大:抗议活动与政策不确定性拖累股汇市场,媒体将其定调为“全国性事件”,进一步放大关注与参与。
六、宗教与政治的“缓冲阀”:社会与权力场如何回应?
印尼传统宗教势力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“降温者”角色。全国两大伊斯兰团体Muhammadiyah与Nahdlatul Ulama(PBNU)相继呼吁民众保持和平,组织集体悼念仪式,为情绪缓释提供了社会接口。
与此同时,总统与国会议长均先后发声,提出“冷静”“追责”“调查透明”等政策信号,试图通过“流程止血”争取舆论缓冲时间。
但问题的深层在于,当“特权制度观感”与“反腐信任缺失”重叠,公众对政治与治理的信任已非一句“依法处理”就能轻易重建。
结语|这不是一次“偶发冲突”,而是一次关于公平与尊严的全国级“应试”
8·28事件之后,讨论的焦点早已超越单一议题的表层。公众追问的,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:国家在制度设计与政策回应上,是否真正重视普通民众的尊严与公平诉求?
过去一年里,从Hasan Nasbi的沟通失当,到Sahroni的歧视性言论,再到Pati县税费激增等问题,无一不在侵蚀普通民众对制度的信任。而对涉嫌官员的特赦与免诉决定,更让这一信任雪上加霜。
Affan之死是一个“引爆点”,但深层火种早已埋下。倘若责任机制不清晰、特权界限不明了,那下次“午后再次聚集、夜里再度爆燃”的循环,还将再次上演。